
湖屿杉山庄,静泊于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鸣鹤镇白洋村的白洋路旁。地图上寻它,需得一番细心;驱车往访,亦需几转几回。它并非招摇的景点,而更像一座被时光妥善收藏的森林秘境。这里是度假村,有步道蜿蜒,有动物栖息,适合友人相聚,团队同行,更适合打掼蛋,品佳茗、尝土鸡、土菜,诗书画歌创作,亦或只是为逃离市声寻一个摄影的角落。周遭有杨梅林远近闻名,夏日来时,想来别是一番红绿交映的热闹。这些描述,勾勒了它的形骸,却未曾触及它的灵魂。我今日随慈溪画家陈新良踏访,所遇所感,远非这寥寥数语可以囊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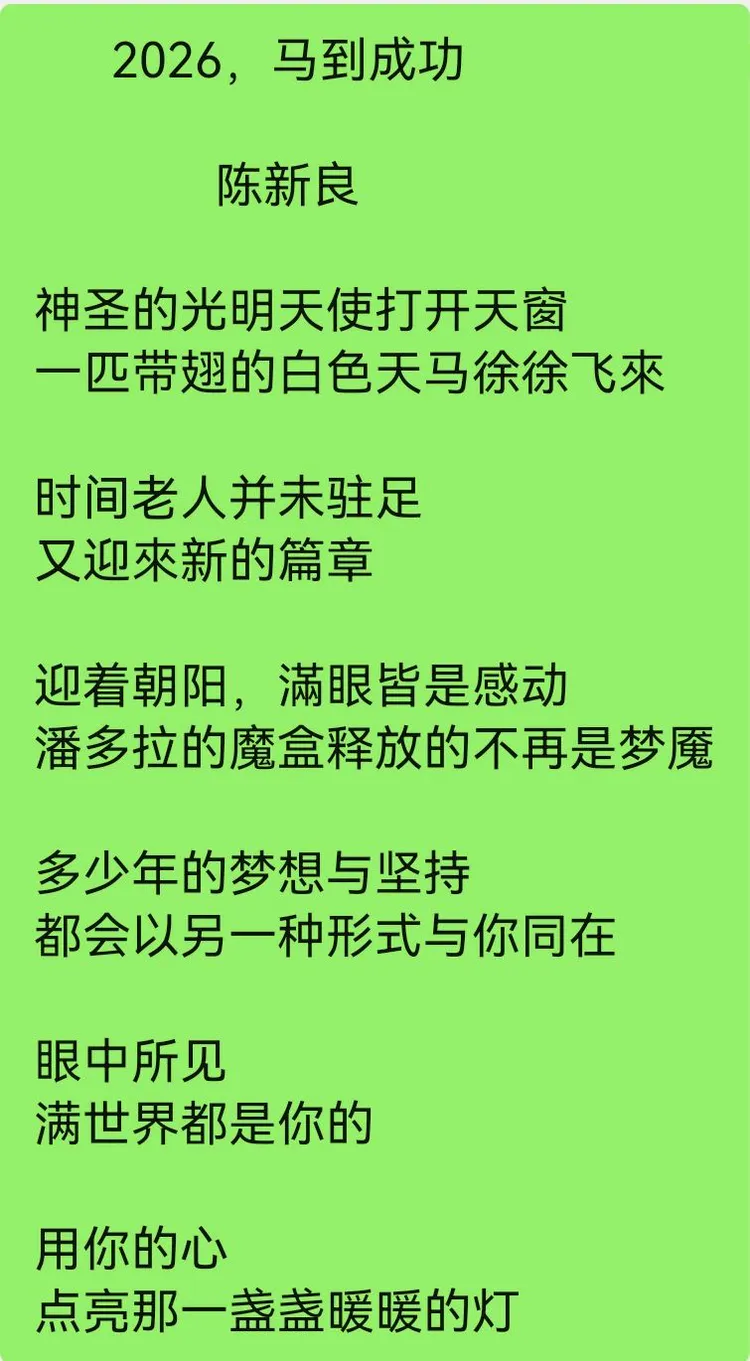
冬阳不是照下来的,是像陈年的绍兴女儿红,被谁从云端里慢慢地、慢慢地倾下来的。光一触到这片土地,便晕开了,融融的,酽酽的,将万物都蒸在一种微醺的、琥珀色的寂静里。我跟在画家身后,踏上那条被芦苇与荒草小心看守的小径。风是凉的,却让那光一衬,反成了酒盅外壁沁着的水珠,只待你去握住那一捧暖。及至叩开那扇虚掩的木扉,第一眼,便撞见了那排闻名已久的水杉树。

它们静穆地耸峙着,枝干挺拔如剑,直指冬日疏朗的蓝天。奇妙的是,那满树的针叶,望去竟真泛着一层若有若无的蓝晕,不是天空的倒影,倒像是画家昨夜离去时,笔尖饱蘸的群青还未干透,被今晨的风一摇,便簌簌地,要滴下些颜色的魂魄来。这便是“绿色景观”么?这“绿”里分明沉淀着夜的幽深与梦的迷离。那呼吸是极沉静的,一起一伏间,将尘世的喧嚣都滤净了,只剩下光与影在针叶间流淌的微响。这哪里是树?分明是一幅从亚麻布上走下来的巨作,抖落了一身的松节油与梦,就站在这风里,等一个能看懂它叹息的归人。那些沿树而设的森林步道,此刻看来,并非为了“建设”或“活动”,倒像为亲近这幅活的巨画,而铺设的谦卑的甬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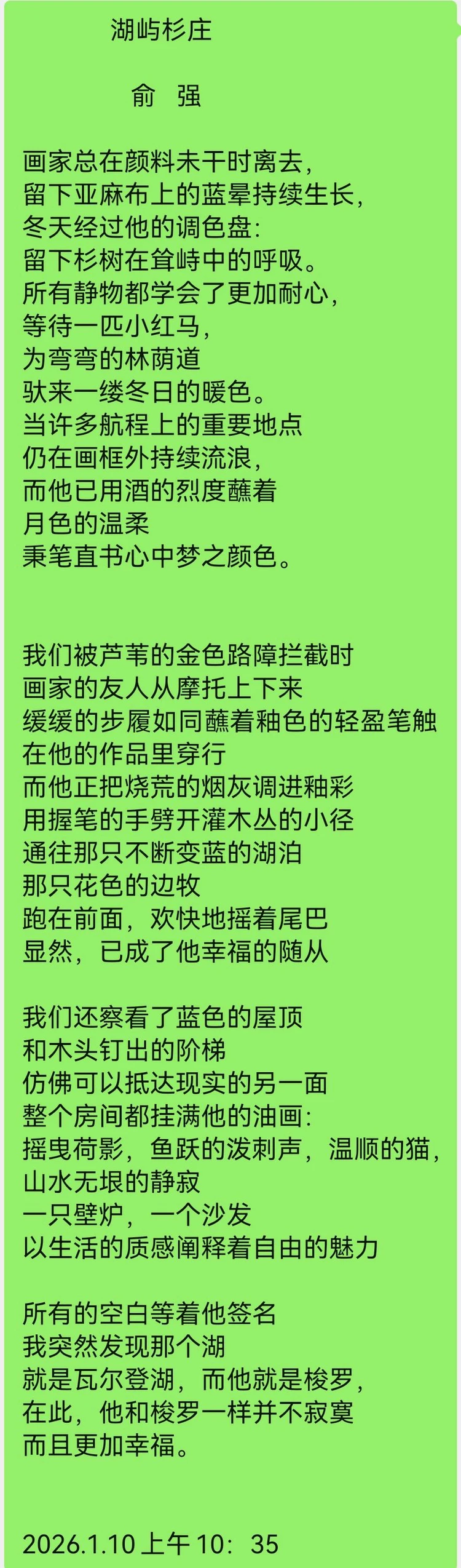
山庄的午餐是质朴而隆重的,“餐饮服务”,却又远超城里酒店。一只山庄自养的土鸡,在柴火与阳光的合谋下,炖成了汤色澄金的一盅天地。然而席间的惊鸿,却是那两碟经了霜的菠菜与青菜。冻伤的菜叶,褪尽了春夏招摇的青碧,呈现出一种谦卑的、墨绿的厚实。送入口中,预期的涩苦并无踪影,反是一股清冽的、直透心脾的甜,软糯地化在舌上。那甜不是蜜糖的谄媚,是大地在严霜的刀刃下,将毕生的淀粉默默转化为糖,一种沉默的、倔强的回甘。许社长举杯,杯中是同样醇厚的绍兴黄酒,诗人俞强说:“霜雪,是大地私藏的糖渍。”我恍然。这一口清甜里,我仿佛真听见了百里外、百年外,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冰面上,“梆”地一声敲开一个窟窿,俯身舀起一瓢凛冽而甘美的自由,用以烹煮他简朴而丰盈的日子的声音。这寻常的“短途休憩”,于此际,竟成了灵魂一次深长的吐纳。

真正的火焰,是在午后燃起的,那是在任何活动指南上都不会记录的章节。慈溪画家陈新良从草地上拖出一大捆枯败的野草,冲我们眨眨眼,那神情像个准备恶作剧的孩童:“点火去?”风正掠过水杉林,发出涛声,我望着那干燥的草垛,心里无端一紧:这火舌若借了风的威势,岂不要将这满眼的“蓝晕”与静谧,都焚作一场壮烈的白灰?新良却笑了,笑容里有种洞悉世情的坦然。他说他几乎日日如此,一手握着画笔,调和着亚麻布上的湖光山色;一手便执这野火,将昨日的枯槁与衰败,坦然地付与一场洁净的毁灭。语罢,打火机点燃,一道金红的弧线坠入草中。

“轰”的一声,不是爆炸,是沉睡的光明骤然苏醒的呐喊。火苗先是试探地、谦卑地舔舐着,旋即仿佛得了号令,轰然跃起,扭动着,舞蹈着,化作一匹光芒四射的、不知疲倦的小红马。它从那诗行里、从画布的想象中挣脱出来,活生生地立在我们面前,驮来的不是虚渺的意象,而是一阵真实可感的、带着硫磺与草木灰气息的滚滚热浪。这热浪扑面而来,竟瞬间击穿了我身上厚重的冬衣与经年的世故,直烫到记忆的深处去——我猛然看见了那个在故乡田埂边,偷偷点燃豆秸的自己,望着噼啪作响的火光,脸上映着同样原始而欢腾的明亮。原来,人过中年与总角童年之间,迢迢数十载的光阴,其距离不过是一簇火苗的跃动;所有被文明规训的谨慎与畏惧,在一堆野火前,竟如此轻易地土崩瓦解,露出底下那颗从未改变过的、向往光与热的赤子之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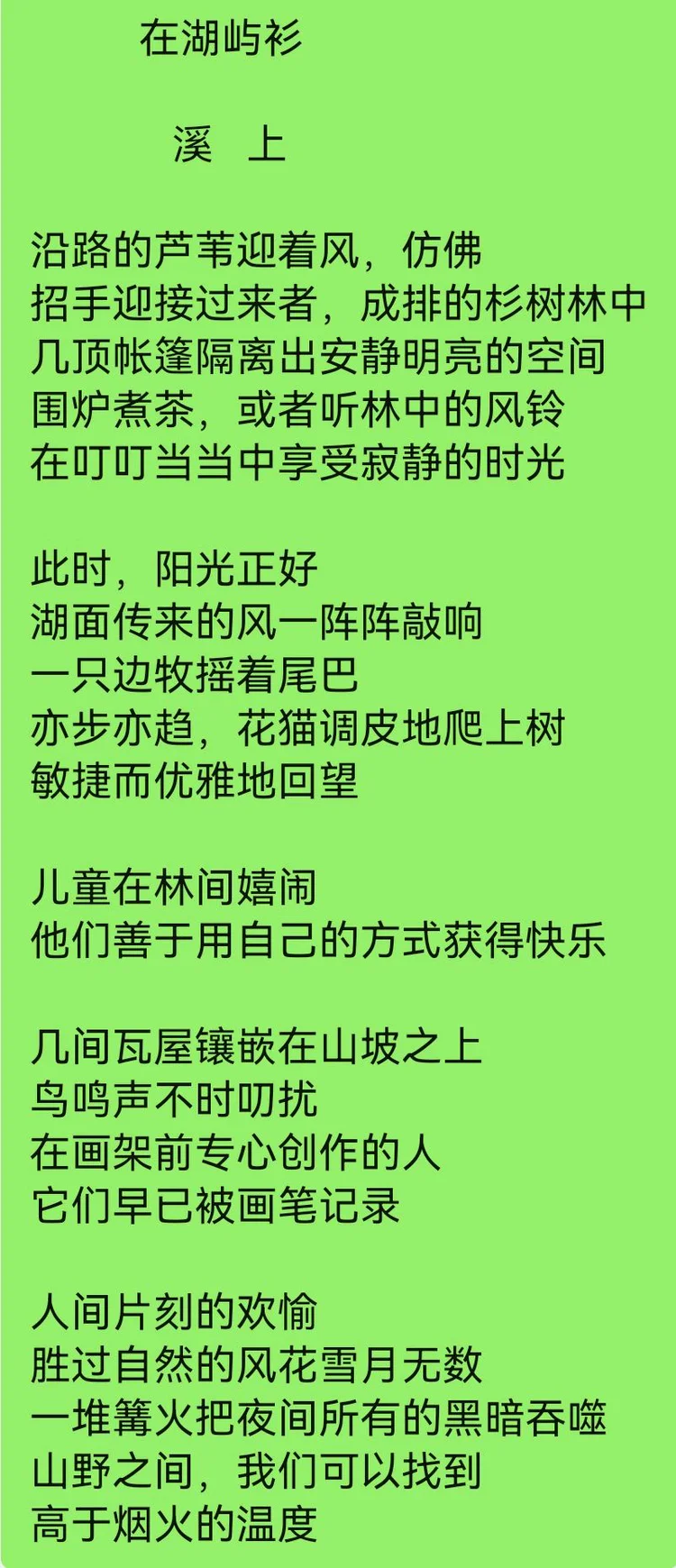
火堆成了我们新的星座,噼啪的爆裂声是它的语言。黄酒的后劲,此刻才循着血脉,温吞而有力地漫上来,胆子像春日的笋,顶着理性的冻土,怯生生地冒出尖来。我们围坐着,身影被拉长,投在身后水杉树的躯干上,仿佛我们也成了这林子里新生的、会说话的植物。话题是散漫的,像火星一样四处迸溅:诗,画,生活。新良谈他的创作,说不仅要画下湖水的蓝,还要将那“烧荒的烟灰调进釉彩”,让灰烬的余温与质感,在画布上获得另一种形式的重生与开花。俞强则沉吟着,说他要捕捉的,是“风敲杉针的声响”,要将那清脆而繁复的节奏,驯服成汉语的平仄,让诗句能够脱去纸页,去林间的空地上自在散步。这番畅谈,比起任何“团队建设”或“朋友聚会”,都更深刻地联结了心灵。 我静静地听着,看火光如何在他们的瞳仁里,投下一粒粒跳动不息的小小太阳。那光如此明亮,竟将平日盘踞心头的种种——房贷的数字,房价拦腰斩的日子,世事的纷扰,光阴流逝的轻响——都照得通透。这些曾如山般沉重的“日常褶皱”,在这野性的、庄严的火光映照下,竟轻盈起来,化作几缕可有可无的青烟,袅袅地,上升,上升,最终飘到水杉树那肃穆的尖顶之上,被那片无言的、广阔的蓝天,静静地签收了去。仿佛天地自有其账本,收纳人间一切微不足道的悲欢。
风不知何时软了,像一个闹够了的孩子,蜷在角落里喘息。火势也渐低,从奔腾的马,还原成一池温暖荡漾的、金红色的湖水。余光瞥见远处,那个真实的湖泊,此刻平滑如一块被岁月反复打磨的铜镜,沉着地收纳着天光、杉影,或许还有我们这几张被火光镀亮的、若有所思的脸。它将这一切繁华与静谧,光影与交谈,都默默地吸入它深邃的怀抱,然后悄悄地将它们揉合、压缩,制成一枚温润的暗扣,别在了大地这袭广阔衣袍的襟前。它是这方天地的印记,也是收纳这一切的锦囊。
就在这一刻,我忽然懂了。湖屿杉山庄,它当然提供资料所述的一切便利与功能,但它真正的价值,远超于此。它并非什么遁世的桃源,更非待价而沽的风景。它是一枚“时间的印章”。它存在的意义,或许就是允许这样的“不合时宜”发生:允许一个画家在颜料未干时便转身离去,将未完的梦境留给风与光去继续渲染;允许一个诗人在酒痕未干时欣然到来,以微醺的敏锐捕捉空气中震颤的诗行;也允许我这样一个在尘世中碌碌推磨的俗客,在这堆野火将熄未熄、人心将散未散的黄昏,猛然与自己失散多年的那个童年赤子劈面相逢,隔着火光,无声地击掌盟誓。 原来,我们这些被种种标签与责任定义的“大人”,穷其一生汲汲营营,内心深处所求的,或许也不过是这样一处地方,几个友人,一堆野火。可以让我们心安理得地、理直气壮地“点火玩”,并在那火光中,找回一种原始的、创造的、与天地直接对话的欢愉。然后,将这光的形状,火的温度,风的言语,酒的醇厚,悉数转化成我们各自的“釉彩”与“韵脚”,留在画布上,诗稿里,生命的皱纹间。 归途,我们一人抱住一只长南瓜,我信手折下一茎枯芦,当作手杖,轻轻敲打着冻得硬实的泥土,发出空空的清响。他说:“走吧。火已经种在我们身上了。”我回头望去,山庄的轮廓已沉入暮霭,那排水杉树只剩下剪纸般深蓝的剪影。唯有我们燃起的那缕烟,细弱,顽韧,像一句斟酌了许久仍未写完的诗,带着无限的眷恋与余韵,弯弯地,袅袅地,升向已现出星子的天际。它是在替我们,向这片收留了我们一日散漫时光的山水,签下最后一个温柔的名字。

于是,我将这一日的所有光景,客观的记述——它的位置,它的功能,它的杨梅林与步道——一并叠好,收入记忆的行囊。然而我知道,真正沉甸甸的,并非这些。此后在某个疲倦的雪夜,或是一段逼仄的旅途上,我会将它们轻轻抖落出来。那时,其中必有一样东西,仍会在我掌心,发出噼啪的、温暖的微响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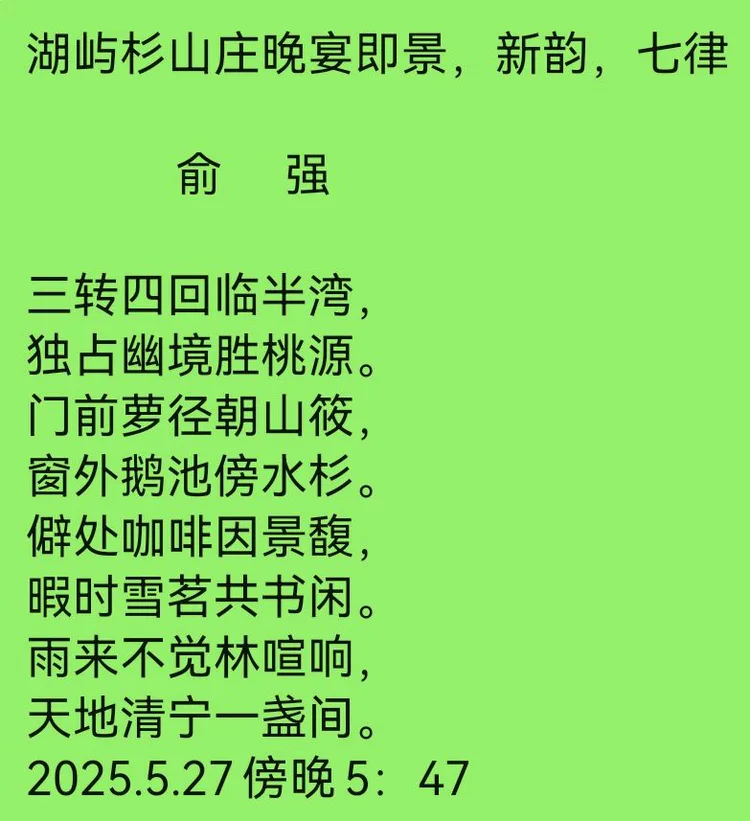
那是湖屿杉山庄赠我的,一粒永不熄灭的火种,一瞥永不褪色的蓝晕,一缕在生命寒冬里,足以熨帖所有褶皱的、永恒的暖色。这温暖,才是它超越一切地理坐标与功能描述的,真正的地址。
本文内容转载自:晨报之声,原标题《作家洪斌:湖屿杉山庄记》,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内容为原作者独立观点,不代表本站立场。所涉内容不构成投资消费建议,仅供读者参考。



